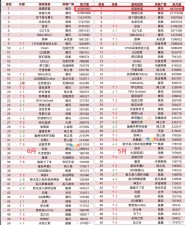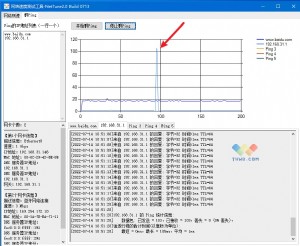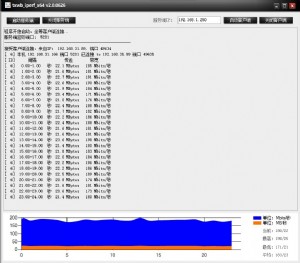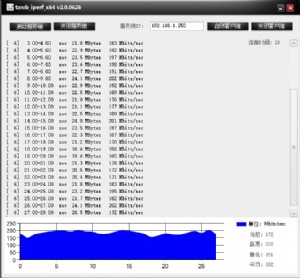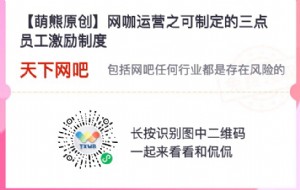比尔·盖茨2013公开信 :谈农业创新和全球健康
让我们看看一位来自达洛查年轻母亲的故事——塞布塞比拉•纳西尔,1990 年出生在自家茅屋的泥地上。由于缺乏救生疫苗和基本医疗保障,当时埃塞俄比亚有约20%的儿童都活不到五岁。塞布塞比拉的六个兄弟姐妹中有四个都夭折了。
然而几年前,达洛查有了第一家乡村卫生站,当地人的生活因此开始发生改变。塞布塞比拉有机会第一次拿到了避孕药具,这使得她和她的丈夫可以选择在最好的时候生孩子。去年,塞布塞比拉又怀孕了,卫生站的工作人员给她进行了常规检查,并建议她去当地医疗中心,而不是直接在家里分娩。
11月28日,塞布塞比拉即将临盆,一辆驴车将她拉到医疗中心。在医疗中心分娩的七个小时里,一位助产士一直守护在她的床边。塞布塞比拉的女儿诞生后不久,便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和结核病疫苗。随后,医务人员将一张儿童疫苗接种卡交到塞布塞比拉的手中,在这张卡片上有她女儿今后需要定期接种疫苗的时间,只要定期接种疫苗,她的女儿就可以免受很多疾病的侵扰,包括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脑膜炎、肺炎以及荨麻疹。
在疫苗接种卡顶端的空白栏,需要填写婴儿的名字。按埃塞俄比亚过去的习俗,父母不会在孩子出生时就为他们取名,因为疾病肆虐、医疗资源稀缺,孩子常常在出生后的几周内就不幸夭折。塞布塞比拉自己就是在出生后的好几周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三年前她生育第一个女儿时,也遵循了这一习俗,因为怕女儿活不了多久,一直等到一个月后才给女儿取名。
不过,自从塞布塞比拉的大女儿出生以后,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相信女儿能活下来,这次,她毫不犹豫就为女儿取了名字。在疫苗接种卡顶端的空白栏,塞布塞比拉写上了女儿的名字——阿米拉,阿拉伯语“公主”的意思。塞布塞比拉的乐观不是一个特例。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成绩显著,与1990年相比,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了超过60%,这为埃塞俄比亚在2015年实现这项重要的千年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绩也给了许多的父母在孩子降生时就为他们命名以自信。
这些故事和案例让我们看到了设定目标以及对效果进行考量是多么的重要。十年前,整个埃塞俄比亚没有农村地区儿童出生或死亡的记录。而去年,我在哲玛纳•盖尔的乡村卫生站看到,包括接种、疟疾病例数等在内的医疗数据图表贴满了卫生站的墙壁。每张表格都清晰地注明了年度目标和季度目标。相关数据会定期输入政府信息系统,并生成报告。政府官员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这些报告进行审查,了解哪些工作进展良好,那些工作还需要更有效的措施来取得进步。
虽然我们都知道对全球健康领域项目进行结果考量的重要性,但如何做好考量却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要做到精确考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开放的氛围,使大家能坦诚地评估哪些工作是有效的,哪些工作不尽如人意。如果我们为免疫以及其他疾病预防干预工作设定清晰的可衡量目标,就可以有效激励政府公共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当然,我们也要尽量防止虚报业绩、数据造假等情况。
埃塞俄比亚最近在全国计划免疫中所采取的“进展监督法”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数据进行跟踪分析,并通过“数据说话”,推广成功的工作方法(这是最难的部分)。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埃塞俄比亚疫苗覆盖率的调查报告显示,埃塞俄比亚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和政府估算的差距很大。埃塞俄比亚官方完全可以忽略这个报告,使用对政府工作有利的数据。然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并没有那么做,他们请来了独立的专家组,探究导致两组截然不同数据的原因。专家组通过详细的独立调查,进一步指出了哪些地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高,哪些地区的覆盖率很低。基于专家组的结论,政府开始制定更完善的方案,以改善效果不佳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
埃塞俄比亚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所取得的进展引起了邻国的关注。而它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鉴了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其他一些国家,如马拉维、卢旺达和尼日利亚,在参观学习了埃塞俄比亚的经验后,也开始逐步开展适合自己国家的医疗推广计划。
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线路图
根除脊髓灰质炎是盖茨基金会的头等大事,也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通过对工作结果精确考量促进全球进步的有力例证。早在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国际扶轮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以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即共同确立了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在清晰的目标引领下,通过政治承诺、资金募集,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伙伴们迅速扩大疫苗接种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至2000年底,小儿麻痹症已经在美洲、欧洲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消失了。
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球新脊髓灰质炎症病例数始终处在1000例以下。然而,彻底根除余下的病例则是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很多类似天花这样的疾病——我们是可以很轻易地通过病人的皮肤症状等进行确诊,然后在病发地迅速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但是脊髓灰质炎的确诊则要经过数周,并且超过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患者没有明显病症,所以病毒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肆意传播。正因如此,脊髓灰质炎被称为“无声的传染病”。在脊髓灰质炎疫情国,为了达到“群体免疫阀值”(通过疫苗接种达到普遍预防某种疾病),医疗工作者每年都要对几乎所有5岁以下儿童进行多次疫苗接种。据估测,在脊髓灰质炎仍然流行的部分非洲和亚洲地区,“群体免疫阈值”的最低门槛为接种覆盖率达到80%到95%。要实现这样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我们必须要有当地主导的、及时精确的考量方法。此外,还需要及时发现哪些地区的接种覆盖率降低了,并迅速找出原因进行补救。
经过与脊髓灰质炎多年的斗争,去年1月,印度实现了全年无脊髓灰质炎新增病例。过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是根除脊髓灰质炎最困难的地区,因为印度城市地区人口稠密,而北部农村地域辽阔,卫生状况恶劣,此外印度流动人口庞大,且每年有超过2700万的新生儿都需要接种疫苗。接种疫苗——这个数字比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每年新生儿数量还要多。但是印度有效地遏制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印度根除脊髓灰质炎是过去十年来全球根除麻痹症运动取得的最大胜利。
目前,全世界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国只剩下三个: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年前,我访问了尼日利亚的北部,我想去探究为什么在那里根除脊髓灰质炎会如此困难。结果我发现那里的常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失效的: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能定期接种疫苗,当然,当地其实也没有儿童数量的可靠统计数据。此外,每次开展接种脊髓灰质炎活动时,当地也无法进行可靠的接种质量检测。整体疫苗接种覆盖率的统计数字更是千差万别。我们决定,要花大力气重新建设一套质量监控体系,并找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们从地图上随机选择一个地区,对当地的儿童是否接种疫苗进行调查。这项调查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独立于接种疫苗的医务者开展工作,以确保调查客观公正。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地很多小型聚居地并没有出现在发给疫苗接种员的手绘地图上,那些地图记录着各村庄的位置以及村庄内儿童的数量。这导致了很多儿童无法接种疫苗。此外,处在两幅地图交界处的村庄常常没有分配到任何医疗接种队。更糟糕的是,很多地图上显示的村庄之间的距离都是主观估计的,有时候竟然会和实际距离相差几英里之远,这让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常常无法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走遍尼日利亚北部的所有脊髓灰质炎感染高危区。通过逐步摸索以及向当地居民了解,他们在当地新增了3000个社区纳入免疫计划。我们现在还通过使用高分辨率的卫星图片,获得了更加精确的当地地图。有了这样的地图,项目管理人员就可以根据村庄之间的实际距离,有效地调配疫苗接种人员,让每个人的工作量都不超过一天。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疫苗接种医疗队根本忘记了前往一些指派地点。为此,我们试点让接种员随身携带配备全球定位系统的手机。每天晚上,接种员当天的行径路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