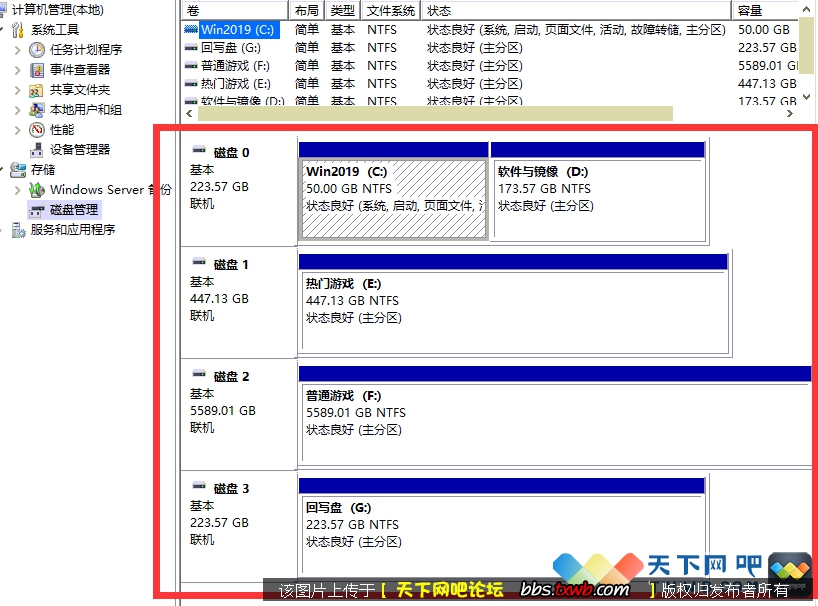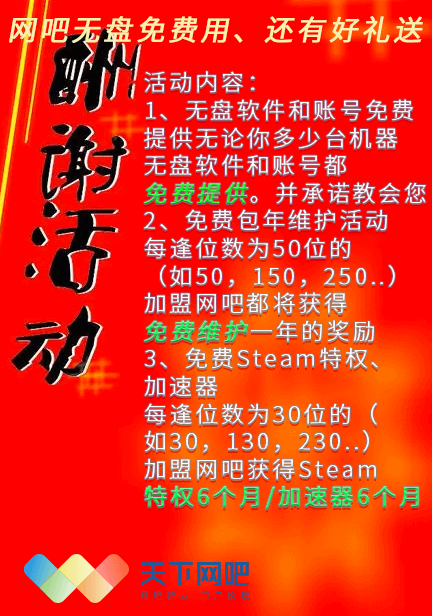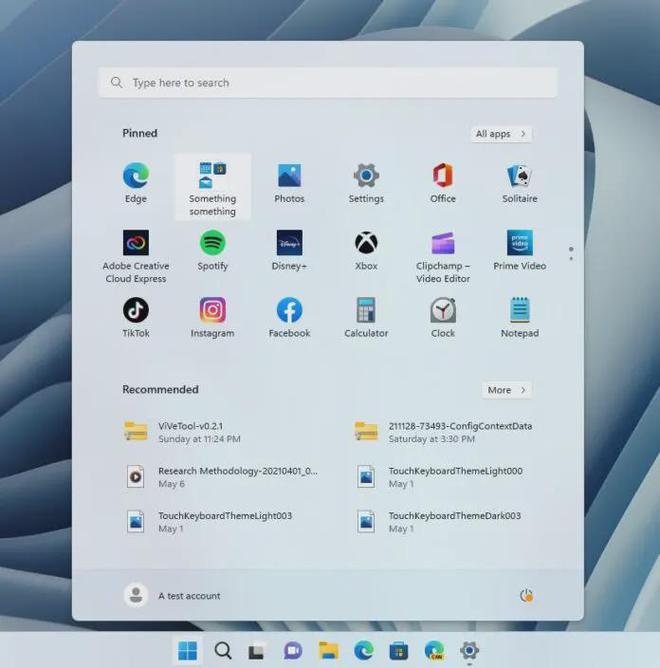男子建艾滋病药品转让平台:信奉商业是最大公益
廖凯将种种迹象与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联系在一起,“他干的事已经变味了。”
程帅帅没有否认在“借药”和代购中,得到了一些在艾滋公寓结识的感染者的帮助。“但那时我还没想做药这方面的事呢。”
他同样没有否认的,是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收益。据他所说,“药品转让平台”几年下来留存的押金有10万元左右,这部分一定会用于公益事业,只不过还没开始正式实施。“可能是资助医科生,或是在西昌建个艾滋客栈。”
而对于代购费用,他则承认,除去往返路费,剩余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收益。“每个月情况不定,好的时候七八千元。”
杭州的阿月也以非感染者的身份做着相关的公益活动,她同样因程帅帅创办“艾滋公寓”的做法有着不错的观感,并且以女儿名义进行过捐款。
当程帅帅最初改变行为方式时,阿月曾对别人说,程帅帅本性不坏,有耐心、有爱心,只是在偏道上越走越远。她不认可的是,将与感染者涉及钱财的药品往来算作公益的理论。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次阿月在微博上言词激烈地批评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提出了举报。微博系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判定,多数人站在了阿月这边。
程帅帅知道,一些曾经的公益伙伴已经和自己越来越远,他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比从前。有感染者来借药,程帅帅曾要求必须转发“药品转让平台”的话题,但被对方拒绝了。有志愿者和他吃饭,也谢绝把两人合影发到网上。“很多人在避免和我扯上关系,确实有点伤心。”
几年前,程帅帅曾在质疑者的微博上甩下一句“看在曾是艾滋公寓的捐助者才不和你们计较”。他说如今自己已很少理会反对的声音,有时甚至会感谢这些反对的声音,每次论战后,“药品转让平台”的关注度似乎都会提高一些。
隐患
程帅帅曾经崇尚高调的公益行为,他为一所知名学府送去过一块牌匾以呼吁教育平等,并因此被警方传唤。他还曾在成都春熙路上缠满绷带行走,通过路人帮忙解开绷带,呼吁反对歧视艾滋病。
如今,这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已经被程帅帅摒弃,因为“药品转让平台”和代购所潜藏的法律风险,他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低调些,避免那些可能太过尖锐的言论和行为。
程帅帅一度很关心有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之称的陆勇的案件,在帮助众多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购买低价仿制药后,陆勇被警方逮捕,但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程帅帅觉得,自己也在做着和陆勇类似的事情,他查阅相关法条,认为自己代购的数量还够不上“走私”一类的罪名,只能算是一种互助行为。
另一方面的规避则来自用词上,即使还药者寥寥,他依然坚持“药品转让平台”外借的属性,对于代购,他则提前在出国前一段时间收取费用,避免钱款和药品上的往来。
但即使当医生的姐姐也不能接受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曾希望姐姐帮忙介绍些有代购需要的病人,被她断然拒绝。
“这毕竟仍然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女儿已经过了一岁,程帅帅还要为家庭考虑更多。对于未来风险的降低,他希望成立一家旅行社,可以组建真正意义的“观光就医团”。
他还拿有几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为陆勇请愿的事情打比方,程帅帅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事情,不大可能有太多感染者站出来为自己作保。
前路
程帅帅说,圈子里还有些人也在做着和自己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愿声张引来注意。而自己的宣扬,则是因为希望更多人效仿这种模式。
他在泰国代购时认识了一位留学生,小伙子已经毕业,但仍往返于国内和曼谷。他不定期地带感染者来就诊,也会靠着当地的关系带进口药回去。
“几个感染者互助组织也都从我这里拿药。”程帅帅说,其中一家“借药”时坚决不收取费用,最后因为没人还药无法维系。他兴奋地把对方的懊恼以及表示将开始收费的聊天截屏发到网上,希望证明自己的理论。
而最初那位和他一起前往泰国考察的感染者,虽然也在做着“借药”和代购的事情,两人却早已分道扬镳。“他嫌我把价格压得太低了,我们理念上有分歧。”
这些与程帅帅行事相近的人物的出现,恰是陈锋等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与国外相比,国内艾滋病免费药物种类缺乏,进口药物昂贵,这是药品倒卖与代购行为出现的根源,却也成为了一个矛盾体般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内药物流通越混乱,政府部门可能越难以放开政策。”
程帅帅自有一套逻辑,他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倒逼”,以越来越多私下药物流通行为的出现为手段,反映出当下艾滋病用药的问题,以促成有关部门作出改变。
有时程帅帅也会想起高调做慈善时赢得的喝彩,他选择否定了自己的那段岁月。他已经订好了到明年连续几个月的廉价机票,目的地仍然是泰国。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