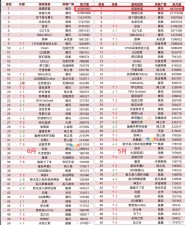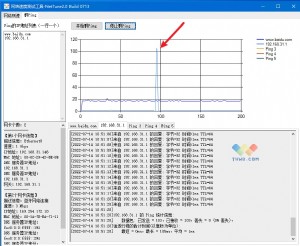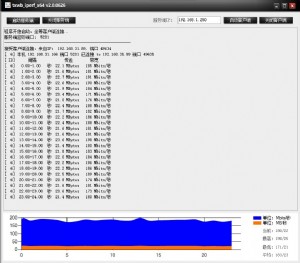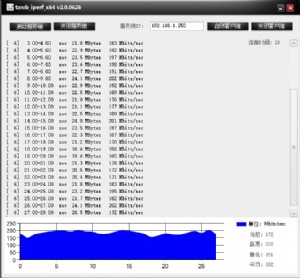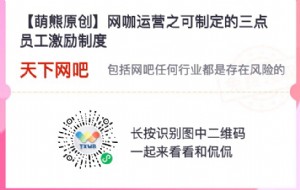Google的中国化生存与中国的世界化生存
声明发出之后,官方报纸《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题为《一件商业纠纷》的社论,强调官方对此事的定性是商业化的。社论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谷歌可能的行动,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商业性的,与政治理念无关。如果这家互联网巨头有政治价值观,那它就不应该从事商业。”
同一天的《中国日报》上,一幅漫画把Google描绘成正在大哭大闹的孩子。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退出?谷歌在撒娇吧!》。显然,漫画和网友评论都在刻意淡化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恰好从反面证明了,Google威胁退出中国,从很多方面讲,都是一件大事。
此后一段时间内,各路人士纷纷登场评说Google的选择: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讨论这一事件是否会重燃意识形态和中国威胁论的忧虑,令中美之间出现某种新形式的“冷战”(或者更精确地讲,可以叫做“温战”);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则关心它是否会波及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并猜测跨国企业今后在华何以自处;有人则抨击审查制度对全球互联网的限制;技术人士担忧黑客攻击所造成的风险,会不会使“云计算”的迅速增长遭受重创。
把这场冲突看得更严厉的人,指称它为影响未来的“第一场信息战”,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Google从中国市场的败退是美国信息战的彻底失败。不知道言者所称的信息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但Google与中国政府间的这场冲突,的确关涉到未来的一个关键资源—信息。
纵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每15年会有一个大的范式转移。1980年是个人电脑,1995年是互联网,2010年则是云计算。我们正在进入下一个创新周期,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整套新工具和新应用,如微软的技术大佬克瑞格·蒙迪所说,随着数以十亿计的“智能”设备联上互联网,互联网演进成为一个威力无穷的计算平台。就如同此前的大型机和个人计算机一样,这个新的平台所支持的应用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随着海量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被收集、存储和分析,复杂的模型将被创造出来,这些模型既可能与大型的社会系统相关,也可能专注于个体的行为。人们通过这类模型,可以预测并且形塑人类社会的下一步发展。谷歌的所思所做,正是集中在这一方向上。它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把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并使之能够被普遍获取和使用”。从全球来看,越来越多的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传送到越来越多的人手中,无论是宽带网、无线通信还是智能终端的普及都在推动这一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们不仅强烈要求接入互联网,而且也渴求随着上网而获得未经阻碍和不加过滤的信息。
既然互联网给予用户对自己想要和不欲获得什么以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事情就变得很清楚,在有关网络内容审查和政策监管的后面,存在的是统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开放的信息则是民众的所求,正如在互联网上流传多年的那个著名的口号所言:“信息渴望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
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不肯退出主导地位的实体—国家,当然不会坐视这种趋势。他们为争夺信息而斗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谷歌宣布了它的非常之举后,很多人不会把此事解读为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企业之间的争吵,而宁愿相信这是两个大国围绕信息时代话语权的博弈。那些更自信个体力量的群体也宁愿把信息视为比想象的国家共同体更珍贵的占有物而努力加以攫取: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环保主义者,都想越过以国家政府为基础的传播通道而让自己的声音为全世界所听到。9
7
3
1
2
4
8
: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