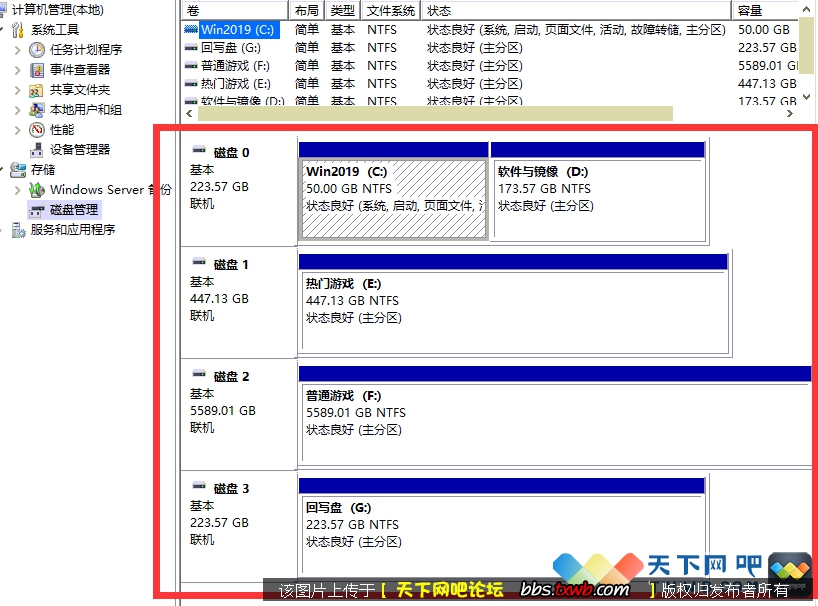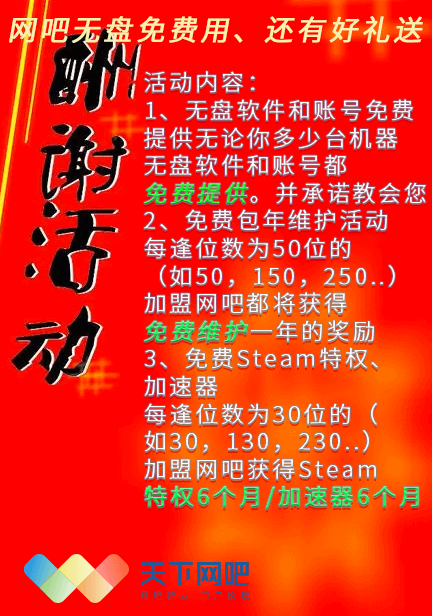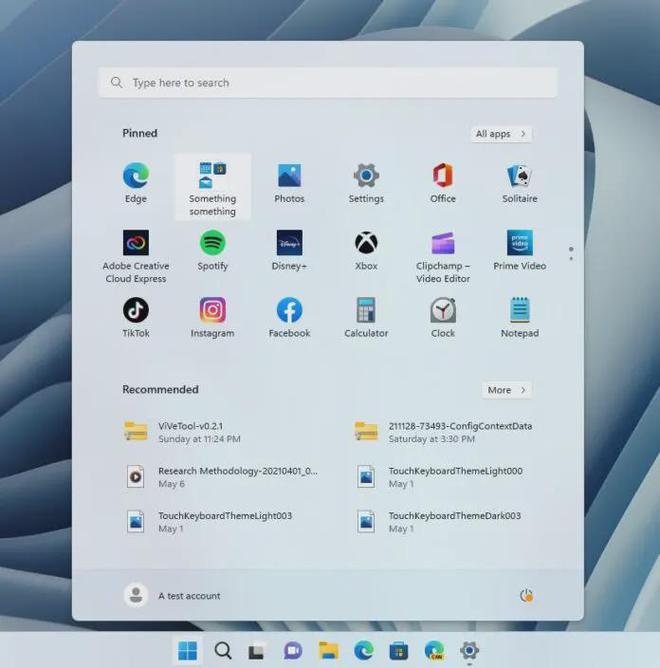“不死”癌细胞背后的秘密
一、“不死”的癌细胞
美国科普作家丽贝卡·思科鲁特(Rebecca Skloot)写过一本著名的科普畅销书《永生的海拉》(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黑人女性——美国南部的一位贫穷烟农,和生命科学和医学史上最早经人工体外培养而“永生不死”的癌细胞的故事。
1951年,作为5个孩子的母亲,年仅30岁的海瑞塔死于恶性子宫癌。医生从海瑞塔身上取走一部分肿瘤组织,开始在实验室中进行人工体外培养,最后得到了一株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医学实验室都会用到的细胞系——Hela(取海瑞塔·拉克斯名字和姓氏的前两个字母),这也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细胞的确能够在体外——实验室里——获得永生,而Hela也成了海瑞塔·拉克斯永恒不朽的名字。

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来源:Harvard University
这并非科学家第一次试图在体外培养人类细胞。19世纪初期,大多数科学家坚信人类或其他动物的细胞都具有内在的永生能力——因血管和器官移植研究而获得19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就是其中一位。
1912年1月17日,卡雷尔把胚胎期的鸡心组织取下,培养在他自制的培养皿里,定期更换从鸡胚提取液中得到的营养成分——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了鸡的寿命。由于人类对“永生”的热衷和好奇,卡雷尔的实验在当时得到了科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卡雷尔也坚定地认为,人体所有的细胞都具有永生的能力,只要给予适合的生长环境和营养成分,它们都能够无限的分裂增殖。

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1912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来源:Richard Arthur Norton
二、“海佛烈克极限”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卡雷尔关于细胞永生的观点,美国宾州费城威斯达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的解剖学家列奥那多·海佛烈克(Leonard Hayflick)就是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1961年,海佛烈克在研究中发现,正常的人类胎儿细胞,在体外培养条件下只能分裂大约60次,而此后细胞群体停止分裂,进入衰老期,最终死去。海佛烈克的实验结果有力地驳斥了亚历克西·卡雷尔“一般正常的细胞具有永生性”的论点。后来,人们把海佛烈克所观察到的细胞分裂停止前所能分裂的次数限制称为“海佛烈克极限”(Hayflick limit)。
海佛烈克的研究发现第一次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癌变的细胞才会永生,任何正常的人类细胞,最终都会走向衰老——卡雷尔体外培养了二十多年的鸡心细胞,不过是在更换鸡胚提取液营养成分的时候,不小心混入了新鲜鸡心细胞的“乌龙事件”罢了。
而“海佛烈克极限”,最终也要与19世纪30年代就早已发现的染色体端粒联系到一起,殊途同归,为我们揭开“细胞永生”的神秘面纱。

列奥那多·海佛烈克(Leonard Hayflick)。来源:RAMIN RAHIMIAN
三、“细胞永生”背后的秘密
端粒是细胞染色体末端的DNA重复序列,它最初的发现和研究,要归功于两位大名鼎鼎的遗传学家:一位是美国细胞遗传学家、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另一位是美国果蝇遗传学家、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约瑟夫·马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9世纪30年代,麦克林托克和马勒通过不同的实验模型,分别观察到细胞染色体的末端存在一种特殊的结构(图1和图3C),马勒将它命名为“端粒”,英文为Telomere,源自希腊文里面的Telos(意思是末端)和meros(意思是组成部分)。麦克林托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如果细胞染色体丢失其末端的端粒部分,不同的染色体末端之间会发生不正常的连接,染色体的结构也会发生异常变化,因此,端粒与细胞染色体保持其结构完整性和稳定性有关。

图1:染色体(chromosome)末端的端粒(telomere)结
然而,麦克林托克和马勒,以及当时其他细胞遗传学家虽然都注意到端粒结构的存在,但没人能够知道端粒的物质基础——它就像一个谜一样的“黑匣子”,虽然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但它却如此陌生,仿佛遥不可及。
那个时候,人们正因为卡雷尔所谓“正常细胞的永生性”论点而激动不已,科学家也还在为染色体上的遗传物质到底是蛋白质还是DNA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基因,在当时的生物学家头脑里还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因此,端粒结构组成的最终揭示,注定要等到19世纪70、80年代——那时候,DNA双螺旋早在1953年被发现,基因在人们头脑里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DNA重组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遗传学研究推进到了分子水平。
1971年,前苏联理论生物学家Alexey Olovnikov,以及詹姆斯·沃森(James Waston)——不错,就是DNA双螺旋的解构者之一、时不时满嘴跑火车的那个沃森——分别意识到,由于复制只能顺着亲代模版DNA 3’端向5’端进行,而且需要一段短的RNA作为引物才能够起始复制,那么经过每一轮DNA复制过程,亲代染色体DNA的3’末端、与RNA引物结合的一段DNA必然因无法得到复制而在子代DNA中丢失。沃森把它称为“末端复制难题”(end replication problem)(图2和图3A),推测细胞中肯定有一种保护机制,防止染色体末端变短愈演愈烈。
而Alexey Olovnikov则进一步提出细胞衰老的端粒假说,用以解释细胞分裂的“海佛烈克极限”问题,认为由“末端复制问题”导致的染色体端粒不断变短,最终会造成染色体的不稳定,某些重要基因丢失,而最终导致细胞的衰老或死亡。

图2:末端复制难题,RNA引物(primer)的降解留下不能复制的3’末端
看来,认识端粒,似乎成了揭示“海佛烈克极限”和“细胞永生”背后秘密的关键!
1975年到1977年间,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运用DNA重组技术,成功鉴定出了单细胞真核生物四膜虫的染色体端粒DNA序列——一段由极其简短的DNA序列TTGGGG组成的重复序列[9]。后来,科学家又陆续鉴定出了其他生物的染色体端粒DNA序列,与四膜虫一样,它们都由简单的DNA高度重复序列组成。例如,人和小鼠的端粒DNA重复序列为TTAGGG,与四膜虫染色体端粒重复序列只有一个碱基的差别。
然而,端粒序列的发现并不能解决“海佛烈克极限”和“细胞永生”的问题。大量的端粒DN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