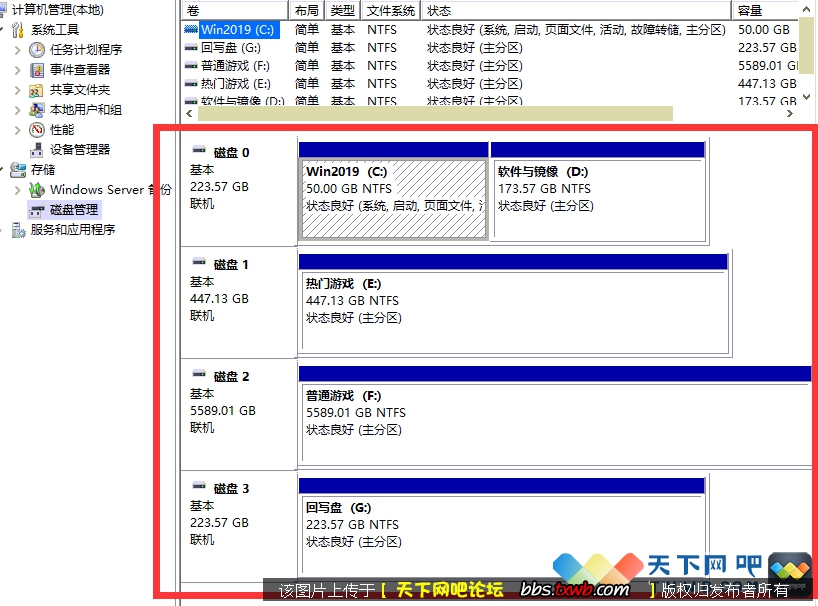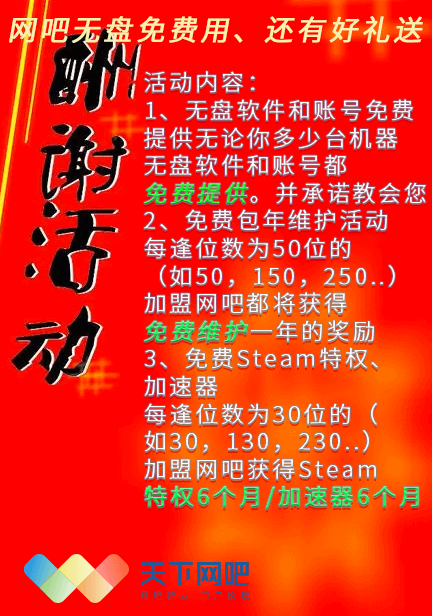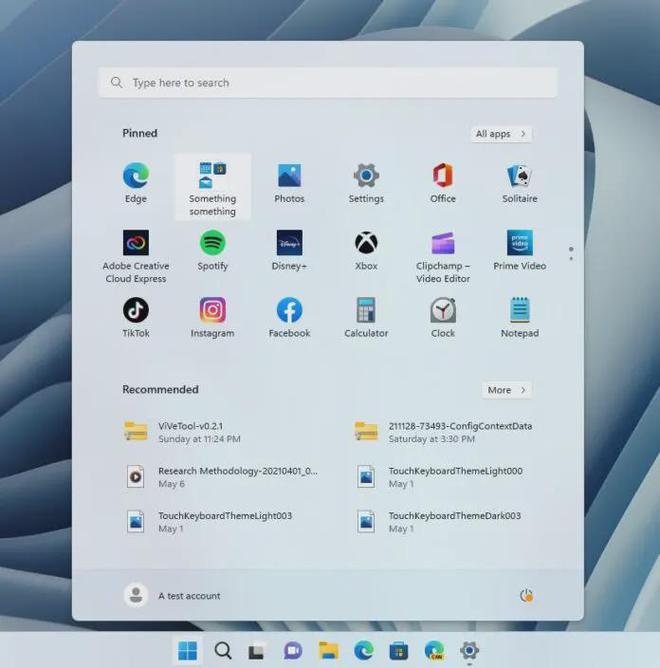接受过“电击疗法”的网瘾少年,如今怎么样了?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五
想要逃脱恐惧的不只有江一帆。
从四院出来后不久,张旭同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听话”的时间。
除了好好学习外,他下课后想去操场转一会儿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气;明明不高兴,见到父母却还要装做“谢谢你们让我重生了”的样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爱情的煎熬——想见女友。但恐惧时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爱情再一次战胜了恐惧,却引发了新一轮恐惧。他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每个角落都有眼睛注视着他,“见女友的事情迟早会被‘四院’发现”。
张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同字,平时大家都喊她“大同”。两人决定去山西大同。
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带手机,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后,来到一个连气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张旭同找了一间10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对未来满心期待。
但恐惧依旧如影随形,他怕“别动队”和亲戚会找过来,再一次被送进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张旭同去劳务中介找工作。因为没有身份证,中介把他推荐到一家煤窑上班,一天赚50元钱。
他和几个皮肤黝黑、身体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面包车前往离大同100多公里的一个矿场。
一路上,张旭同还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矿场,电视节目里出现过的谋财害命的黑煤窑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后来,他应聘过耐克店的店员,因为多唠叨了几句“不给加班费”,被人告状后,“硬气”地辞职。他也重操过旧业,在游戏厅里打金币和装备赚钱,可依旧入不敷出。
他说,在那半年多里,没有一点漂着的感觉,“至今觉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
可当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时,他最终还是选择向父母求助。
回来后,张旭同没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换不同的地方睡觉,睡觉前在门口放一个空酒瓶,有人开门瓶子就会倒地。
“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