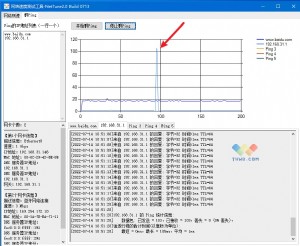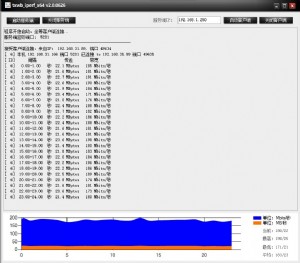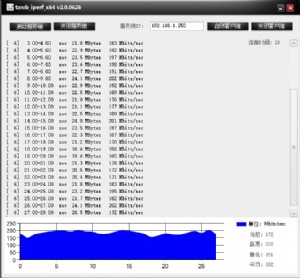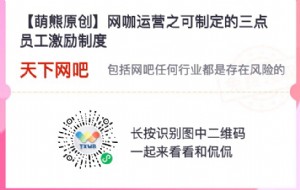比尔 - 盖茨:一个改变世界的计划(全文)
软媒注:本文为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应邀担任《连线》杂志2013年12月期荣誉编辑后撰写,英文原文载于《连线》。
我对化肥有点儿着迷,当然我着迷的不是化肥本身,而是它的功效。我常常参加一些很严肃的讨论农业化肥的研讨会,也读了一些关于人类如何收益于化肥,同时受害于化肥的书籍。我想像我这样喜欢化肥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尽可能提醒自己:“比尔,千万别在鸡尾酒会上大谈化肥。”
但就像每个人都点儿小癖好一样,我觉得我对化肥的喜爱是有充分原因的。当今世界上,五分之二的人能够活着,都要归功于化肥带来的粮食产量提高。化肥是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加速器,而那一次“绿色革命”让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数以亿计的人们因此免予饥饿并脱离贫困。
最近这些年,我投入了很多时间,希望通过促进像化肥这样的创新改善人们的生活。抱歉再罗嗦一次——今天世界上40%的人们要感谢1909年德国发明家弗里茨·哈伯发现了合成氨的制法,由此我们有了化肥,并提升了农业产量。另一个创新改善人类生活的例子是,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在过去的25年间下降了99%,并非脊髓灰质炎自己远去了,而是因为阿尔波特·萨宾(Albert Sabin),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并在全世界的大范围推广和接种。
感谢这些创新,人类今天的生存条件大幅改进。当然也有人会从反面反驳,比如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有10万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可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今天,无论从什么指标,我们都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战争频率是有史以来最小的,人类的平均寿命较一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上学的孩子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就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类似脊髓灰质炎疫苗、化肥这样的突破性创新。道理很简单:创新让世界更美好——更多的创新意味着更快的进步,正是这个理念支撑着我和梅琳达,以及我们基金会不断前行。

创新千差万别。而我和梅琳达希望我们对社会的回归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的投入能够得到最好的回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着手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并找到和推广那些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解决之道。这听上去简单,但做起来困难。首先,我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什么是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面对贫困、疾病、饥饿、战争、教育不公、政府腐败、社会动荡、贸易不畅、以及性别歧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我和梅琳达则选择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贫困、疾病,与教育。这个选择源于我们的父母从小教育我的理念:每个人的生命都享有同等的价值——众生同值。抱着这样的理念,我们快速扫描世界哪些地方的人们,无法和我们一样享受生命的价值。而这些地区和领域,我们能够做出巨大的改变,我们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将我的财富回报社会。微软的成功让我拥有了很多财富,我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去花好这些钱。当时,我阅读了很多关于政府在基础科研投入不足的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帮助科学家在实验室对世界进行基础性的研究,下一代的创新就会失去基础。因此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能够创办一个机构,资助最优秀的想法进行尝试和实践。

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事件让我决定投身公益,如果非要追溯的话,那要回到1993年我和梅琳达的一次非洲之行。当时我们原本是计划与一个狩猎队前往那里看野生动物,然而最后我却看到了真正的极端贫困。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车窗外,一队非洲女性排着长长的队伍,头顶着装满水的容器缓步而行。我当时想,她们每天要这样走多远呢?她们来取水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呢?
这次经历让我对世界最贫困的人们有了第一次直观接触。1996年,我父亲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发给我,这篇文章说,全球每年有100万孩子死于轮状病毒,然而在富裕国家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病。一个朋友给我了一份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里面详尽描写了全球儿童疾病的各种问题。
看到这些问题,我和梅琳达都惊呆了。尽管富裕国家一直在静悄悄地给于对外援助,但很少有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大药厂不会为穷人需要的疫苗而大规模投入。报纸也不会报道贫困地区的儿童死亡。
当我认识到这些现实,我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改变世界。我一直是一个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并相信这是最好能够同时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制度。这个制度带来了众多改变世界的创新,并可以将其迅速推广,提高数十亿人的生活,比如飞机、空调、以及电脑等。
然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穷人的需求。这已为这市场导向的创新不但不会惠及穷人,反而会扩大贫富差距。2009年,我在南非德班的一个贫民窟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巨大。露天的小便池在提醒我们这一行从富裕国家前来的人,我们每天理所当然使用的冲水马桶并非人人可及,全球25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厕所,每年有150万儿童因此死亡。
政府对创新的驱动力也乏善可陈。政府对于创新,尤其是穷人需要的创新一直投入不足。原因很简单,政府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有能导致自己的下台,而大量基础性的研发工作都面临着极高的失败风险。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放弃了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的想法,并开始转向那些商业、政府都投入不足,或不愿投入的领域。从这时起,我与梅琳达一起开始了新的征程,我们管它叫作——催化剂式慈善。
催化剂式慈善的理念与操作方法和商业市场类似:都是追求最大的投入产出比。但两者又有巨大的差异,在慈善公益领域,我们的投资不追求金钱的回报。我们的工作方法是:(1)缩小差距,便于富裕国家能够更方便地援助贫穷国家,(2)鼓励更多的创新力量关注并解决贫困国家面临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工作也存在挑战:我们是在全球范围内,面对数以兆亿的市场中博弈,面对这样的市场量级,任何一个公益机构都是相对弱小的。如果我们希望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找到一个杠杆的支撑点——能让我们投入的每一分钱,以及每一分钟,都可以放大一千倍惠及全社会,这就是我所说的“催化剂式慈善”。
其中一个重要支点是投资那些市场和政府不愿意投入的领域。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梅琳达开始投入全球健康领域。当时大量儿童因为无法接种麻疹疫苗而死亡,而这种疫苗只需25美分,我们只需要投入相对很少的钱,就有机会拯救很多孩子的生命。疟疾也是如此,当我们第一次投入疟疾研究时,我们的捐款几乎等于当时全球疟疾基础研究的投入总和,我们的捐款其实并不多,你可想而知当时疟疾研究领域投入不足的程度。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为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好点子提供种子基金。我们知道很多尝试都可能失败,但我们填补了政府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风险承担者,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有部分创新取得突破,就有机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当然,当这些创新取得突破后,政府则可以参与进来,扩大生产规模和覆盖范围。
我们同时也可以引入市场主体,因为绝大部分创新来源于企业。有些人说未来的经济是后企业家,或后资本家时期,届时大型企业会肢解,而创新


本文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