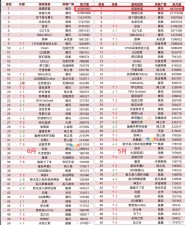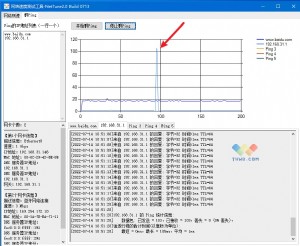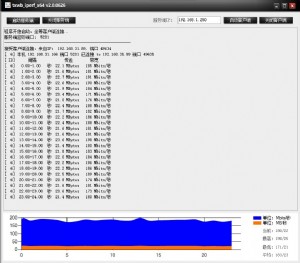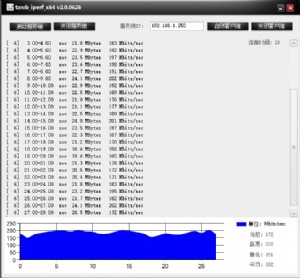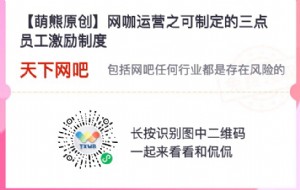现代科学发展已经导致天才人物灭绝?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校长基恩-西蒙顿称,就如同不幸的古代巨鸟一样,这种类型的科学天才已经灭绝了。西蒙顿在自然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写到:“未来的进步很可能是根据已知的东西而不是基础知识的改变。”一个世纪以来都没有真正的原始科目被创建出来,相反的是新生科目都是与现存的相混合,比如说天体物理学或者生物化学。他争辩道,以个体身份做出突破性贡献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前沿的科学研究通常都是由资金充足的庞大团队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已经为一场革命做好准备。只有理论物理学展现出一种转折点的信号,未知发现的积累为它带来了一种思考模式的重大转移。”这并非是第一次有人预测科学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之前,两位理论物理学家并不能够达成一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哲学副教授Sherrilyn Roush指出,19世纪的科学家们曾预言全部的主要发现已经完成。
Roush在一封写给生命科学的邮件中说到:“革命和天才就像事故一样是不可预言的。通常直到它们露面你甚至才知道你需要它们。”她并不赞同西蒙顿的理论,她声称对于革命来说天才未必是决定性的。虽然西蒙顿称天才出现的机会减少,但是他认为科学的需求正在增长。他写道,考虑到现在的研究人员成为专家所需要的信息量和经验,当今的科学家要成为成为一名一流的研究人员,或许比成为16世纪和17世纪“英雄时代”的一名天才需要更多的原始信息。Roush对此表示赞同,她声称现今阅读一个特定领域全部发表的作品可能已不再是可行的。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