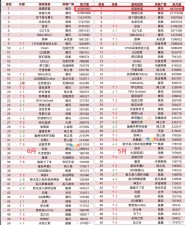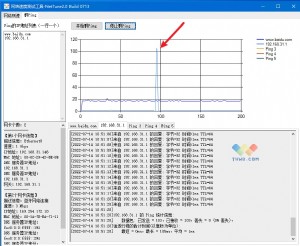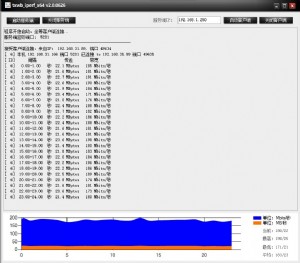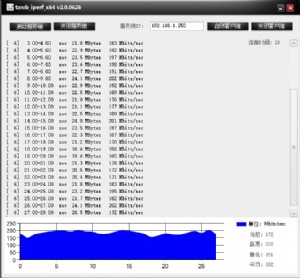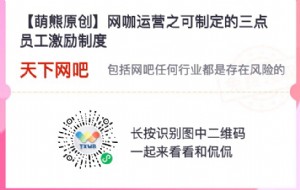揭秘全球电子垃圾坟墓:地球在滴血
站在电子坟墓上,斯坦利久久无声,注视着那一片片剧毒的烟雾飘向自己,飘向远处。
B=《外滩画报》
SG=斯坦利·格里尼
“我们的文明让我们成了这些短命商品的奴隶”
B:是什么促使你在2009年后开始进行这个横跨大洲的拍摄项目?
SG:起初,我和Noor的摄影师们一起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选题。我的任务是去拍摄北极圈里面的爱斯基摩猎人,关注气候变暖对他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境况让我震惊,不仅仅是冰雪消融让猎人们一无所获,更在于他们和北极动物的家园正在被一艘艘货船向这里倾泻的电子垃圾侵蚀。于是,我试图寻找这一切发生的根源,为什么人们要在这里倾倒电子垃圾。为此我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越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开始,我原本计划去拍摄五个国家的电子垃圾问题,包括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它们的问题最严重。但是后来我看到很多摄影师已经去加纳拍摄过,我不想重复,所以最终选择了另外四个国家作为我这个追踪电子垃圾项目的拍摄目的地。
B: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SG:作为一名摄影师,我想了解在这些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地的人们为什么要去接收这些来自西方的电子废物,是什么样的利益驱使人类建立这样的电子坟墓。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当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严峻问题。即使是现在,当我把照片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你拍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因为这些电子垃圾,一些人的健康正在恶化,正在死去,失去生存的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则把这些毒物看作是一种有趣的玩具,比如越来越高科技化的电脑、手机。在很多地方,人们努力工作,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拥有更新的玩具,然后把那些旧的扔掉,送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文明让我们成了这些短命商品的奴隶,然后成为被自己生产的垃圾剥削、损害的生物。我不可能阻止这一切,但我试图用照片延缓这种速度,这种发展的速度。
B:在拍摄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SG:虽然我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但是当我真正踏上这片电子垃圾场的时候,我还是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这里就像一座巨大的黑色坟墓,里面充斥着来自西方文明的电子残骸。生活在坟墓里的人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淘金的乐土。
B:在采访中,你同样受到电子垃圾的毒害,难道你不害怕么?
SG:我喜欢挑战那些有难度的报道选题。在格陵兰的时候,同事们说我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里的冰川美景,这或许能够让我从那些恐怖的战地报道中解脱。但是,当我站在冰川上,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电子垃圾。后来我发现,是一艘艘的货轮将这些垃圾运到了这里。
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的实习生、助理和我一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是电子垃圾的最主要去处。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可怕的电子垃圾,那些曾经代表着时代最进步科技的东西,正在危害当地人的健康,甚至置人于死地。这太恐怖了。再后来我们还发现,这些电子垃圾同样带来诸如童工问题、奴隶问题等等反人道的犯罪。我的脑海中一直有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宽敞的屋子,堆满废弃电脑主板,一位瘦弱的老女人在熔炼它们,可她暴露在外的双手已经由于长时间被化学毒素侵蚀而开始腐烂。
“我的责任就是一名信使”
B: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SG:在我采访的一个小镇,整个镇子居民的收入都来源自这些电子垃圾,所以这是不可逆转的。我的一些朋友,拥有五个手机也属正常,所以我无力改变,只能尽可能地去让它变缓。另外,你可以在那张巴基斯坦拍摄的照片里看到一些政府或大公司的警示画,在警告人们从事电子垃圾回收是对个人身体有极强危害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作品,警醒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得不从事这项危险的工作的时候,注意对身体的保护。
我希望那些生活富足的人们可以通过我的照片,了解到他们随手丢弃、更换的旧机,对其他人或许意味着很多。作为一整个电子产业链中的一环,你们必须关心生存于同一循环中的其他人。我们是人类,有人性,所以必须小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会伤害他人。我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用手机、不要用电脑,而是说,制造者应该生产更加耐用的产品服务社会,而消费者应该把这些电子产品当作工具而不是玩具,不喜欢了就当作垃圾丢弃。
B:拍摄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找到合适的“向导”?
SG:这个拍摄需要充分的前期调查。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的,所以我会向朋友、同事询问,谁认识那样的人,可以帮助你进入拍摄地。有时候,你就径直走向离你最近的那辆出租车停靠点,也许那个司机就能够成为你的好向导。或者去大学,也许一些希望通过兼职来赚些钱的大学生能够带给你意外之喜。有时候,一些陌生人会主动给我写信,希望能够参与到我的工作中来。在尼日利亚的时候,我的线人告诉我,那里的垃圾场都是黑帮控制的,很危险。可实际上,那里的黑帮也都是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组成的,他们对我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收成”。
B:一些照片中人的表情往往带着一丝愤怒和忧心?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电子垃圾的受害者?
SG:不,他们仅仅把这看作一项可以让自己吃饱肚子的工作。让他们不开心的原因,可能是迟迟没有发的工钱,而不是对身体健康的担心。而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同情。在尼日利亚阿杰甘勒垃圾场,废弃的电子产品被有序地归类和清洁。一大群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长期居住于此。其中一个男孩打扮得好像迈克尔·杰克逊,面对镜头他跳起了太空舞。可是他告诉我,自己曾经在一次提炼电路板中的金属时,不小心引起了大火,烈火给他的脖子和胸口留下了伤疤,同时带走了他的脚趾。可是如今他仍然一边买卖电子垃圾,一边模仿当红歌星唱歌跳舞。
B:在回到工作室后,你对那些胶片作品是否满意?
SG:我希望能有机会去拍摄那些电子产品,比如电脑、手机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即记录它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但是很遗憾,那些大公司不允许,另外我的资金也不够支持我独立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报道项目。为了目前的拍摄,我花费了37000欧元。
B:纪实摄影师的责任?你的摄影哲学是什么?
SG:我的责任就是一名信使,我把发生的事实用照片讲述给大众,让人们知道在那些公司精美广告和政府宣传的背后是什么。我的摄影哲学非常简单,就是去现场,把黑白是非呈现出来,寻找黑暗中人性的光芒,或者在光下寻找人性的黑暗。所以我常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观察那里的人的行为,去寻找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动因。
文/刘旭阳 摄影/StanleyGreene/Noo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