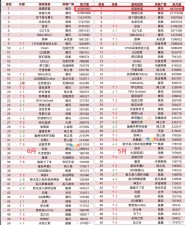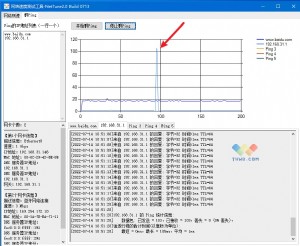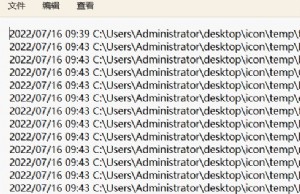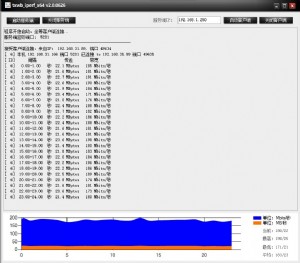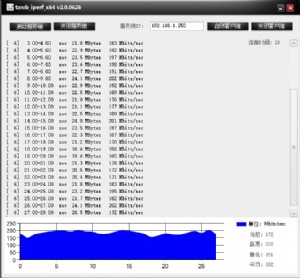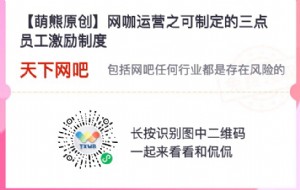走近Google X负责人特龙:硅谷创新精神不死

国外媒体今天刊登前对冲基金经理安迪·凯斯勒(Andy Kessler)的文章称,虽然硅谷的创新能力逐渐受到质疑,但仍然不乏激进的改革派,他们正在通过很多突破性的技术打破常规,希望以高远的志向推动社会发展。
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毕生信念
惠普裁员2.7万人,雅虎陷入泥潭,Facebook IPO跌落神坛。硅谷创新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工程师是否只会开发千篇一律的iPhone应用?
我知道,有一个人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驳这些观点。
他所在的办公楼门口凌乱地摆放着各式各样颜色花哨的自行车——红、蓝、黄、绿,颜色与谷歌的Logo相映成趣。此时此刻,我正站在神秘的Google X总部门口,在这里,谷歌将众多难以置信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作为这里的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带着我们来到一间陈旧的会议室。房间内的椅子都漆成了一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绿色,隔壁房间不时传来桌上足球玩家的欢呼声。45岁的特龙身材高瘦,穿着当地一家创业公司的灰色T恤,语调轻柔,带着典型的德国口音。
“我感觉像是从远洋邮轮上跳到海里学游泳。”他的开篇如此说道。
特龙拥有德国伯恩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这在53所德国计算机学院中排名倒数第一。”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他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但却未能成功——原因是他采用了基于规则的研究方式,但人类永远不可能为机器制定所有必要的规则。不过,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机器开始像婴儿一样通过不断摸索掌握“自主学习”能力,这一领域再度繁荣。
特龙90年代中期离开德国,前往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导师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让他“选一个对社会有益的方向”。所以,他决定开发机器人,包括护理机器人和导游机器人,前者可以在家中照顾老人,后者已经在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接待了数以千计的游客。要帮助机器人了解现实世界,需要展开跨学科教育,涉及的领域包括护理学、心理学、材料学等诸多领域。虽然这些项目都很困难,但他说,“放手去试,相信你的学习能力,不要墨守陈规——这是我毕生的信念。”
他最终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方向,带领该校的团队参加了200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以下简称“DARPA”)的Grand Challenge挑战赛,内容是创造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在沙漠中行驶132英里(约合212公里)。他坚持不向学生灌输既有思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们从未接受过这种抛弃一切前提假设的训练,这很可悲。”他说。斯坦福最终以11分钟的优势胜出。
在DARPA的挑战赛上,他遇到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他当时戴着墨镜和鸭舌帽隐藏在挑战赛的观众中。佩奇聘用了特龙和他的团队,他们加盟谷歌之初从事街景的开发。但特龙的任务很快发生了变化:“佩奇经常找我吃饭,他每次都会做一番畅想,而且很激动。我的反应很明确:这根本没戏,有很多漏洞。但我回家后还是做了细致的计算,于是,一天或一周后,我会向他道歉:‘你完全正确。’”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无人驾驶汽车,但不是穿越沙漠,而是在旧金山的街头行驶,甚至还会开到其他地方。这很疯狂,但特龙和他手下的12位工程师曾经开发了一辆汽车,在没有人类驾驶员的情况下轻巧地穿越了伦敦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要质疑所有的规则,要打破这些规则。”他说,“我喜欢把自己置于最难受的境地。我们的包袱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有勇气抛掉一切。”
社会责任
但我还是很好奇,谷歌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我认为谷歌的定位是,我们有责任为世界做一些精彩的事情。我们从没讨论过这个项目如何帮谷歌赚钱。”他说。
这或许源于内在动力。该团队只有12名工程师,我猜,整个项目的花费还不到5000万美元。换句话说,相比于高达800亿美元的底特律救助计划,这还不到1/1000,但却足以改变整个汽车行业。
与无人驾驶汽车相比,谷歌其他项目的好处显而易见——通过新颖的服务颠覆了有线电视或图书出版行业。但特龙却坚持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对社会大有裨益。”因为这项技术能够拯救被心不在焉或技术不佳的人类驾驶员夺走的宝贵生命,每年有数千人因此丧生。“所以,我们怎么能放弃这个项目呢?”他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没有人类驾驶员参与的情况下行驶了数十万英里。
在Google X,特龙聘请华盛顿大学教授巴巴科·帕维兹(Babak Parviz)开发了一副能够显示网络内容和谷歌搜索结果的眼镜。这同样很困难,为了降低重量并简化使用体验,同样需要面临跨学科挑战。这有点像双光眼镜,向上看即可获得内置芯片提供的内容,避免遮挡正常视线。“我们发现这并不是空想,我们距离这个有趣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这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每个极客都渴望这样一副眼镜。
我试图打探其他Google X项目的消息,但却未能成功。特龙表示,“这些项目都具有科学挑战性,但前提是必须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要具备可行性,还要克服巨大挑战。”智能手机应用太简单了,“佩奇经常鼓励我们志向高远。”
事实上,特龙始终不安于现状,他说:“我会花一整天爬山,然后只用10分钟领略美景。”
在线教育
但他仍然很愿意谈论一个项目。他和另外一名谷歌员工彼得·诺维德(Peter Norvig)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人工智能,苦于只能容纳200名学生,他们创办了一个网站,专门提供在线课程。开始的参与者不多,但后来,他们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在线课程,与会的80人全部注册了。到了周五,他们将这条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个人工智能协会的会员,周六早晨便收到了3000份注册申请,周一早间达到1.4万。
在此过程中,特龙碰到了一些问题,他说:“我忘记通知斯坦福了,他们质疑我的职权。斯坦福说,‘如果你给他们的考试和结业证书与斯坦福一样,你就破坏了制度。他们会拿着结业证书申请大学,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究竟是谁?’我说:‘我不在乎!’”
最终,有16万人注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朝鲜。这些课程并没有采用简单的说教,而是要求学生解决问题,然后在下一堂课中讨论解决方案。特龙再次打破常规。最终有2.3万人完成课程。在200名注册该课程的斯坦福学生中,只有30人参加课堂教学,另外170人全部通过在线授课。考试得分最高的410人都来自在线课堂,排名第一的斯坦福学生仅位列411。
特龙的课程花费很低,人均费用仅为1美元,还不到常规K-12(从幼儿园到高三)或大学教育的1/1000。根据硅谷的经验,通常只需要10倍的成本优势即可推动变革。
所以特龙创建了一家名为Udacity的公司,与其他公司合作优化在线教育。“我认为大众化的教育将改变一切,”他说,“我对此充满激情。我们将接触到永远接触不到的学生。我可以把我自己对学习的热爱传递给他人。我已经步履蹒跚地进入了最奇妙的仙境,领略过其中的景象。”
“但仙境很疯狂!”我打断道。
“那又怎样?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我会利用在谷歌的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我真的很在乎。”特龙的这个项目可能会彻底颠覆既有教育模式,对公共学校、教师工会、大学教授等各种利益团体构成冲击。但他表示:“人们讨论问题时总是担心会对机构产生什么影响,我却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
我问他为何非要改革,而不改良?他说:“这是谷歌教我的——志向高远。Udacity是我的地盘,我要在这里展开激进的实验,然后查看结果。我已经看到了曙光。”
如今,特龙的讲话方式已经像是一名真正的硅谷企业家。“人工智能课程是第一缕曙光,在线教育将超越当今最好的教育,而且价格更低。如果能够成功,我们就将大幅加快社会和世界的发展。”他说。
我见过很多像特龙一样的人,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应对如此艰巨的挑战时,他们都会反问:为什么不呢?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
天下网吧·网吧天下